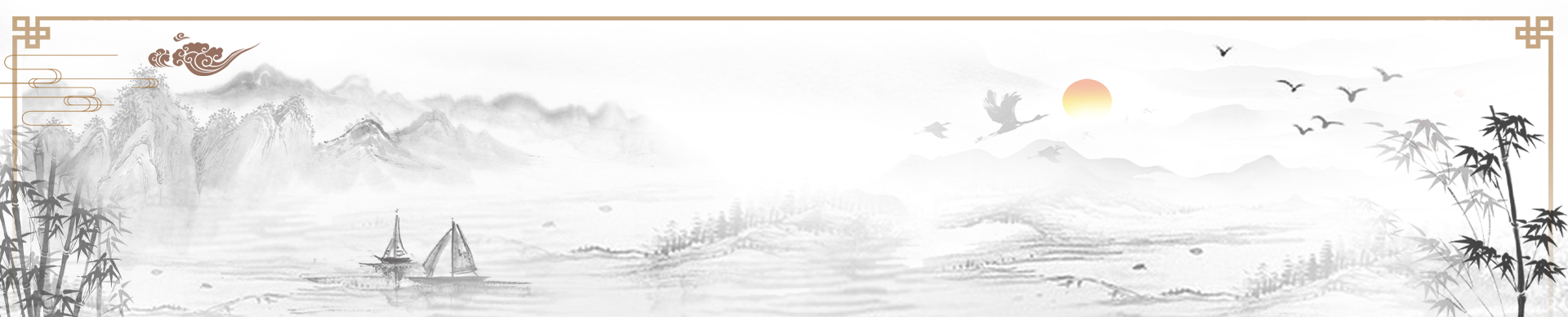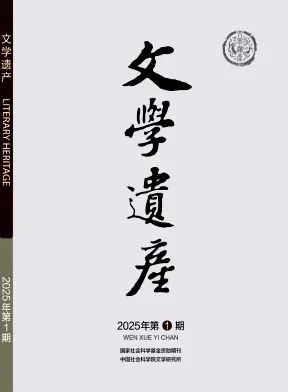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25年第1期。
《聊斋志异》西传欧美与“异”的跨文化表征
任增强
内容提要: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是拥有外文译文语种最多的中国古代小说。在近200年间的西传进程中,“异”成为汉学家翻译与研究《聊斋志异》的聚焦点与叙述主线。由于时代语境与问题意识的不同,汉学家对“异”的认知呈现出多个层面的话语转换。在中西接触的早期阶段,西方汉学家对《聊斋志异》多有曲解;至19世纪末,出于全面认知中国社会生活的诉求而借《聊斋志异》以观风俗之“异”;20世纪以降,则希望借助《聊斋志异》深入探究中国民族性格、文化基因与思维方式等。欧美汉学将“异”作为理解他者与观照自我的双向链接点,最终将《聊斋》之“异”从民族性文学经验提升至世界性的话语资源,在跨文化语境中丰富了对《聊斋志异》的认知。
关键词:海外汉学 《聊斋志异》 欧美传播 文化表征
清代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因作者蒲松龄“研精训典,究心古学”“行文驱遣成语,运用典籍”,文字雅驯古奥,对普通读者而言存在一定的阅读障碍,如清人孙锡嘏在《读〈聊斋志异〉后跋》中言道:“书中之典故文法,犹未能以尽识也。”(《〈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第495页)袁世硕先生也曾指出,由于受制于文言这一语言载体,《聊斋志异》的影响力远逊于《水浒传》《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但如若将学术目光投向海外,则会发现另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即“中国古典小说中,《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就英语世界的情况而言,自英国伦敦的《弗雷泽城乡杂志》(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于1835年推介《聊斋·白于玉》故事,其后历经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翟理斯(Herbert A.Giles)、乔治·苏利耶·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Morant)、马丁·布伯(Martin Buber)、邝如丝、张心沧、闵福德(John Minford)等汉学家的翻译推介,至21世纪20年代美国汉学家蔡九迪(Judith Zeitlin)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计划推出四卷本中英双语版《全本新译详注聊斋志异》(Liaozhai's Strange Tales: A New,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可以说近200年来《聊斋志异》在欧美地区几乎不间断地在翻译和传播,得到了英语世界汉学家乃至普通读者的持续关注。也就是说,文言文这一小说的语言形式,并未妨碍《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由此也自然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是基于何种动因促使海外汉学家对《聊斋志异》持续产生学术探索的热情?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在于《聊斋》之“异”。“异”,作为一个意涵丰富的话题,长期以来成为读者的“一种强烈爱好”,在海外汉学不同问题意识的烛照下凝析出了不同的文化表征,由此成为欧美汉学认知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学经验。
一、《聊斋志异》之“异”的理解向度与汉学聚焦
何谓“异”?据《说文解字》,“异,分也。从廾从畀”。这里已然指出,“异”具有区分与不同的意思;在《康熙字典》中,“异”又出现了诸如“又不同也”“又怪也”“又奇也”“又违也”等解释。这些释义呈现出了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首先,在《康熙字典》中“异”的意涵较《说文》更为丰富,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异”的释义方式又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阐释循环,因为“异”“怪”“奇”是常见的近义字,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界认。对此,有学者就认为“很难精准地对“异”做出一个明晰而充分的定义,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异”可以界定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第7页)可见,与其徒劳地追问“异”的本质,不如在认知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联系中重新审视“异”的生成。正如东晋郭璞在《山海经叙录》中所言:“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在此,郭璞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视角,指出“异”并非为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而生成于阐释者的主观理解之中。依循这一思路,可以说《聊斋志异》在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海外汉学家对“异”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进而促成了近200年来这部文言小说集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的持续热度。
倘若细加梳理《聊斋志异》的百年英译史,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异”是绝大多数海外汉学家对这部小说的学术聚焦点与兴趣点所在。虽然《聊斋志异》书名中有“异”,但并非所有的汉学家均关注“异”这一现象。比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Wells Williams)于1842年出版的汉语学习教材《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以及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对《聊斋志异》则有“Pastimes of the Study”的译法,完全规避了“异”,侧重的是《聊斋》优美的文风与纯正的汉语;无独有偶,英国汉学家禧在明(Walter Hillier)在其所编著的汉语学习教材《华英文义津逮》(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第二卷中将《聊斋志异》译作“Liao Chai”,关注的是其内容和文风,亦未着意于“异”这一问题。在此,卫三畏、禧在明等偏重的是《聊斋志异》的艺术性问题,而“异”更多的是一个涉及社会意涵与文化表征的问题。
较早在英语世界译介《聊斋志异》的《弗雷泽城乡杂志》(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虽未直接给出《聊斋志异》的英译名,但署名为“Δ”的文章作者在评述《白于玉》时,使用了“the marvellous”(惊异)、“genii”(鬼怪)的说法;而后德国汉学家郭实腊于1842年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撰文,使用的是“Extraordinary Legends”(奇异传说)的表述;20余年后,英国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在《中日释疑》(Note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撰写“The Record of Marvels;or Tales of the Genii”(《志异;或曰鬼怪故事》一文,“异”依然是其关注的焦点。欧美汉学家对“异”的聚焦,最终以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9世纪末对《聊斋志异》的英译“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而基本固定下来,即援用英文中的“Strange”一词与“异”加以对译,并影响到了后世的西方汉学家。诸如法国汉学家德·莫朗于1913年推出的英文节译本,题为“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1989年,美国汉学家梅丹里(Denis C.Mair)与梅维恒(Victor H.Mair)的节译本题为“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2006年,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的节译本作“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2008年,美国汉学家宋贤德(Sidney Sondergard)的全译本,题为“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直至蔡九迪的研究专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Historian of the Strange: 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围绕“异”这一话题作了更为深入的阐析。
至于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1911年推出的德文节译本和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邝如丝1946年推出的英文节译本,中文名同为《中国鬼怪爱情故事》;英国华裔汉学家张心沧推介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中国文学,题为《中国文学:超自然故事》(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以上三个译本虽未使用“Strange”一词,但是“Ghost”与“Supernatural”的说法,亦足以显示出海外汉学家对“异”的关注。
二、由《聊斋》而观风俗之“异”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较早在欧洲开启了研究世界各国风俗文化的先河,他于1756年在日内瓦出版《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一书,致力于了解“各主要民族的精神、风尚、习俗,以及一些为了说明这一切而必须了解的事实”。出于现实需要与学者的推动,欧洲逐渐围绕“风俗”形成了一门学问,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as)率先提出“民俗学”一词来指称这门新兴学问——旨在对普通民众的各种信仰与风俗开展研究。而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全球化的初步成型,欧洲本土所兴起的这一“风俗学”思潮必然会影响到来华西人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这一方面体现为西人开始逐步深入中国内地,开展一系列民族志式的实地调查与探访,撰写了大量与中国民俗及国民性格相关的著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借助翻译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以了解更为广阔和真实的中国社会生活。
具体到《聊斋志异》,上文所提及早期来华西人虽开始关注这部通俗小说,但基本是转述性的,其间包含了对原材料的选辑、重塑乃至曲解,借用翟理斯的话,很多中国的风俗遭到了反复奚落与抨击,原因在于虽然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但几乎没有哪部著作所传递的信息是第一手的;换言之,几乎没有一部书是让中国人自己言说自我的。鉴于此,翟理斯重设了译介中国知识的目标与意趣,即通过翻译《聊斋志异》这一让“中国人自己言说自我”的方式,向西方读者全面而客观地介绍中国社会的风俗人情,从而与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等汉学家一道,共同建构起了另一种观照《聊斋》之“异”的认知方式。
《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小说集,包括了近500篇故事,“记录了大量明清之际的风俗文化事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代风俗画’”。正如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所言,小说与传奇故事充满了风俗与生活画卷最为精微的细节,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翻译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在这一理念影响下,翟理斯担当起了《聊斋志异》的大规模英译工作,他在华生活长达25年,谙熟中国语言文化,对汉语语法结构有着精准的认知,并且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信仰与一般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洞悉。翟理斯选译了164篇最具特色的故事,这其中既有《蛙曲》《鼠戏》等短篇志怪,亦包括《考城隍》《劳山道士》等长篇传奇故事,全面展现了异域社会的百态世相;尤值一提的是,翟理斯除借助译者序言外,又充分发挥注释媒介的功用,通过随文所下的逐条注释将《聊斋志异》正文中不易为西方读者所理解的民间信仰、节气时令、生活习俗等相关文化内容进行更为详实准确的介绍,由此帮助西方读者对古老中国有了近距离的了解和认知。正如他在再版序言中所说,作为对中国民俗学知识的补充,和了解这个庞大国家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的指南,他的《聊斋志异》英译本或许并非完全没有趣味。
循着翟理斯观风俗之“异”的翻译之路,法国来华汉学家德·莫朗于1913年推出了《聊斋志异》英文节译本,共选译25篇故事,同样涉及长篇传奇如《画壁》《海公子》,以及《山魈》《荞中怪》等短篇志怪故事。德·莫朗的翻译并非完全忠实于原文,而多为改写之作。比如第二篇故事“The Fresco”即《画壁》译文,在文中他增添了诸如“令敝寺蓬荜生辉”“不敢,不敢”等宾主见面时的寒暄语;第三篇故事“The Dwarf Hunters”即《小猎犬》,他在开篇又增饰了诸如中国南方的湿热气候、蚊虫对病人的困扰等有关内容。德·莫朗之所以在翻译中增加各类风土人情的描写,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全方位地借助小说和故事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社会生活的具体样貌。这一点,德·莫朗在译本前言中有着明确的说明。他指出,在学堂之外,中国人对儒家经典的关注并不比西方人对西方经典的关注多:倘若看到中国读者手中所捧之书,那绝非《大学》或《论语》,而更可能是诸如《三国演义》,抑或鬼故事集一类的小说,它们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比所有儒家经典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小说与故事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独特的作用,而这却是外国人所极少或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在此,德·莫朗对单纯译介儒家经典的传统汉学路数作了进一步的反拨,强调了小说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与民众生活的重要性。
有西方学者曾这样评价翟理斯的汉学成就,即他赋予了世纪之交的英国一个微妙却有着显著变化的观察中国的视角,这不但消解了西方读者将中国文明作为异国情调的做法,而且由此开启了不同民族之间富有意义的交流之旅。西方读者对《聊斋》之“异”的产生,缘于资本扩张后对新发现的地理空间在经验与知识方面的不足,而借助翟理斯、德·莫朗等汉学家的文化阐释与知识传递,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风土人情逐渐进入西人的视线与脑海中,最终变得不再是“异国情调”式的存在,因为“鼓励我们去寻根究底的,与其说是事物的伟大,毋宁说是它们的新奇”,然而“眼睛看惯了,心灵也习以为常。我们不赞羡常见的东西,也不去寻求究竟”。而这一由“异”变“常”的进程也正是中西之间互识与互解的文化交流过程。
三、鬼怪爱情叙事背后的文化符码与《聊斋》之“异”
全面了解相异于西方文明的中国社会,“观风俗”显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模式,但是风俗的背后又有一套深层次的支配性话语系统。随着中西方在经贸、政治、文化间频繁地接触,西方对中国必然会产生更为深层次与纵深化的认知需求。自19世纪末以降,一些西方来华的有识之士不断基于大量经验性体认与理性思考对中国文化开展深入探究,如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等著作,除细致考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外,也开始讨论中国人的思想性格与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对《聊斋志异》的译介也逐步朝纵深化推进,由此对“异”这一话题衍生出了新的认知路径,即从反理性主义的视角审视《聊斋志异》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民族性格、心理定势与世界观。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高扬理性,在不断向外探索自然与改造世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带来了人的精神危机与自我失落,从而将目光转向东方文化寻求理论资源,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由此展现不同价值诉求的《聊斋志异》再次进入了西方汉学家的视野中。
(一)《聊斋志异》与布伯的哲学探思
最早经由译介《聊斋志异》而探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是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布伯于1911年推出德文节译本,共选译16篇《聊斋》故事,题为《中国鬼怪爱情故事》。其中10篇转译自翟理斯译本,另外6篇为布伯在助手王警涛协助下完成的,这16篇故事于1991年又由阿里克斯·培志(Alex Page)转译为英文,并由以色列汉学家伊爱莲(Irene Eber)撰写导语。布伯本人不通晓中文,其译介《聊斋志异》旨在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资源,以印证自己的哲学主张。在《我和你》(Ich und Du)一书中,布伯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他通过探讨“我—你”与“我—它”两种关系范畴,借助经验世界与关系世界的区分,对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之间”说。“我—你”关系存在于两个能动的主体之间,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两个主动主体之间的相遇和对话。而经验世界中的“我—它”关系是片面的,“我—你”关系才更能实现完整和纯粹。“我—你”关系不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更存在于人与万物之间,是全面而有爱的联系。而布伯所选译的《聊斋志异》中“最为优美和最令人好奇的关于人类与鬼怪的爱情故事”,恰恰展现了其他民族同类故事所不具有的亲密感与和谐感。在此,人类爱上并拥有了鬼怪,同时鬼怪亦爱上并拥有了人类,没有神秘与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自然的秩序并未断裂,反而得以延伸(Chinese Tales, p.111)。可以说,布伯在借《聊斋志异》论证其哲学见解的同时,也阐明了《聊斋志异》所蕴含的独特思维方式与世界观,正如伊爱莲在译本导语中所说,中国思想中的整体观念是关于无所不包的一种秩序,含括了此岸与彼岸世界。这两个世界、社会政治秩序与鬼神的秩序,彼此间并非完全隔绝,它们以一种奇特的、不期而然却又绝非混乱的方式开展互动。
布伯以哲学家的学术敏锐力对《聊斋志异》中这一潜隐的男与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关系发微阐幽,也影响了后来的邝如丝、闵福德等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
(二)“我—你”视域中的《聊斋》“男—女”关系
《中国鬼怪爱情故事》亦为澳籍华裔汉学家邝如丝所译《聊斋志异》的英文节译本书名。该译本选译了40篇故事,与布伯《聊斋志异》德译本同名。而且,在征得布伯同意后,邝如丝移录并英译了布伯德译本的序文。作为女性译者的邝如丝在翻译中构建了独特的女性话语,体现于她在布伯“我—你”框架下重新打量《聊斋志异》中的“男—女”关系。在布伯看来,“我—它”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我”是主动者,而“它”则是被动决定的。“我”是经验与利用“它”的主体,“我”作为主体,具有对象化的能力,而“它”不过是对象而已。具体到男女关系中,女性不过是男性欲望化的对象,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被支配者,由此揭开了西方近代以来两性之间的鸿沟,一种对立而非交融式的关系。
邝如丝的译文充分挖掘了《聊斋志异》中“我—你”框架下、非西方式的男女关系处理方式。《画壁》作为《聊斋志异》中一篇著名的故事,历来为英译者所垂青,翟理斯、邝如丝、闵福德均曾将其收录在各自译本之中,但对其中男女情爱的处理却迥然有异。原文描写朱孝廉与拈花仙女见面时,言道:“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对此,邝如丝的译文处理,既非翟理斯式武断地剔除原文所有的感官体验,又非闵福德男子中心主义式地渲染男性观感与占有欲,而是翻译为:他(她)们的心顿然间欣喜若狂。在此,邝如丝所欲展现的是朱孝廉与仙女彼此在爱慕与尊重的相遇中身心融合后的两情相悦,是男女对等的参与和体验。这既不同于翟理斯为“观风俗”而改写为:他们跪下拜天地,起身结为夫妻;亦非闵福德译文将女性作为客体对象的一味占有,即:他一下抱住了她,发现她毫无拒绝之力,接着便占有了她。邝如丝借助布伯“我—你”框架对《聊斋志异》中“男—女”关系进行挖掘,让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读者发现了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式的东方两性关系。
(三)闵福德的怪异叙事翻译与阐发
如果说邝如丝的翻译侧重于从“男—女”两性爱情角度切入,以“我—你”关系为框架探查《聊斋志异》所呈现的性别观与价值诉求,那么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则对《聊斋志异》怪异叙事背后的世界观多有关注。
闵福德在翻译时发现,《聊斋志异》在汉语语境中常被称为“鬼狐故事”,书中仅有极少数故事如《尸变》《喷水》《山魈》《咬鬼》等属于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怪和超自然故事,更多的情况是鬼魂作为女性复活者,施展媚术与人相爱,并精通房中之术。闵福德举例说,《莲香》篇讲述书生与狐仙和女鬼的三角恋情,即便其中有些形而上的对话,亦不过是探讨人类与异类如何相爱的。特别是经过前半段的争风吃醋后,狐仙莲香与女鬼李女竟然变得亲如姐妹,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妻妾间的和睦。
在列举《莲香》为证后,闵福德又回到布伯的论点上,指出《聊斋志异》中很多故事虽与鬼怪和其他超自然力量有关,但一方面鬼狐的形象指向的是人间,象征着两性之间的殊死较量,缠足以及道教的采补术便起源于此;另一方面,这些所叙的怪异之事,跨越了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畛域,在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中,此岸与彼岸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而非如西方世界中那般泾渭分明。
在此,闵福德承袭了布伯的洞见,由哲学层面说明《聊斋志怪》故事背后所展现的东方世界观。正如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所言,“中国语言—思想特别能表达那种隐然的状态一就是当这个“大地一隅”把自己建立成伙伴,那推动它的张力就把我整合到它里面而与我分享。换句话说,当我与“大地”建立了(恢复了)某种关系,这关系让我回到认知性的理智所建立的事物的上游——在那儿找到它的源头”。由此,不同于西方的鬼怪故事,超越二元对立的整体性思维模式构成了《聊斋》之“异”生成的一个文化符码。
四、结构性认知与《聊斋》之“异”
寻绎《聊斋志异》叙事背后的文化符码,是汉学家审视《聊斋》之“异”,进而探究异质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的重要向度。肇始于马丁·布伯的探查,这一审视《聊斋》之“异”的研究路径最终在张心沧与蔡九迪的著述中形成了更为明晰化的结构性探析。
(一)价值诉求与功利层面的“异”
张心沧,原籍上海,英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其译介《聊斋志异》的代表性作品即《中国文学——超自然故事》。作为张心沧推出的中国文学六卷英译本中的第三卷,该卷选译了唐、宋、清三代的文言小说共12篇,其中关于《聊斋志异》的译介占了全书近乎三分之一的比重。张心沧选译了在他看来最能够代表蒲松龄艺术才能的四篇故事——《窦氏》《黄英》《乐仲》《促织》,并借鉴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寻绎出《聊斋志异》中潜隐的四类价值诉求:金榜题名、娇妻美妾、贵子贤孙、生活富足。这些均为清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蒲松龄的心理欲求,以及其结缀《聊斋》故事的基本逻辑。作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小知识分子,蒲松龄虽屡困场屋,但始终未曾放弃对金榜题名和荣华富贵的幻想,这种功利性意识决定了蒲松龄必然会着眼于现实利害与世俗欲求,并通过写作这一“白日梦”式的活动注入《聊斋志异》故事中,成为普遍性的叙事逻辑。冯友兰依据人觉解的程度将人生分为四重境界,即所谓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而“金榜题名、娇妻美妾、贵子贤孙、生活富足”显然属于世俗层面的“功利境界”,不甚高远。当然《聊斋志异》并非停留于此,如《考城隍》《瞳人语》等篇,清代评点者何守奇认为“赏善罚淫之旨见矣”(《〈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第380页),自然是处于“道德境界”;而涉及“天地之境”的篇目,则有《婴宁》《顾生》《寒月芙蕖》等。因此张心沧的结构式解读与发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若从跨文化视角观之,“金榜题名、娇妻美妾、贵子贤孙”对西方读者而言显然体现出了一种文化之“异”。
(二)三层结构关系与“异”的再认知
如前所述,“异”是《聊斋志异》持续引发欧美汉学家关注的一个核心要素。历代西方汉学家在翻译中不断揭示“异”的跨文化意涵,近年来蔡九迪《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出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又加以深化讨论。
《异史氏》一书在对整部《聊斋志异》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拈出了三种关系,即“癖好(主—客)”“性别错位(男—女)”与“梦境(幻—真)”,认为《聊斋志异》因对上述界限的跨越,或者说因传统的界限和范畴通过某种方式被扭曲、改变,从而产生了“异”的叙事效果。这一对“异”之生成与意涵的新发现,也受到布伯“之间”说的影响。如蔡九迪指出,“过度僵化的分类会造成各种错误的二元对立”,《聊斋》之“异”“必须要在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变动区域中加以界认”(《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第12页)。结合明清之际的文化语境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的多种社会学与文学理论,蔡九迪对“异”作出了新的解释。她发现《石清虚》故事中爱石者邢云飞与石头之间并非纯粹的主客二元关系,而是“双向奔赴”的对话与交往关系。邢云飞为石头不惜舍弃田产、家产,乃至三年寿数;而石头则在梦境中与他攀谈,在他死后竟然将自己摔成碎片以与知己者生死相始终。由此,主客之间的界限被完全抹平。而此岸与彼岸间界限的跨越,则集中体现在《画壁》故事中。主人公朱孝廉飞升至寺内壁画中,与垂髫的拈花仙女相欢好,当他返回世间时竟发现画壁上出现了拈花人螺髻翘然的影像。拈花仙女原本作为少女的发式变为了已婚女性的发髻,证明此岸与彼岸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
如上所述,如果说主客合一的整体观、此岸与彼岸间的相互通约性是《聊斋志异》所呈现出的东方文化之“异”,那么性别的流动性则显然是东西方所共同出现和关注的文化现象。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曾说:“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最终要看:这个文明塑造了什么样的人,塑造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唯有一个文明所塑造的男人和女人,才能真正展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这个文明的灵魂。”蔡九迪显然也是抓住了这一关系到“文明的灵魂”的两性问题,经由对《颜氏》《商三官》《乔女》等篇的解读,发现在《聊斋志异》中大丈夫气概被重新评定为一种真正的道德品格,无论女性或男性,均可以通过自我修养和正义的行为来获得。颜氏女扮男装,科考高中;商三官扮作伶人,报杀父之仇;乔女走上公堂,挺身而出报答赏识自己的男性。这些行为无不有悖于传统道德对女性行为的规约,但蒲松龄正是通过跨越传统所设定的性别界限,进而展现了中国古代女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这一点如波伏瓦所言:“一个生存者除了所做的事,什么也不是;可能性不会超越真实,本质不会先于存在:人从纯粹的主体性上来说,什么也不是。人们根据其行动来衡量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故事中对女性的界认,以及对父权的颠覆与解构暗合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潮,由此吸引了汉学家的关注。当蔡九迪等西方汉学家将目光投向《聊斋志异》中此类有关性别越界的故事时,其对“异”的关注已经远非“观风俗”或发现东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而是基于同类的问题意识而向东方寻求可借鉴的资源,旨在理解自身的文化现象。但正如费孝通所言:“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在这一转向东方的过程中,蔡九迪恰恰将中国文学的经验提升为“一个普遍的信息”,将《聊斋志异》“异”这一话题赋予了世界性意义,由此成为东西方之间思考共同性话题的有效话语资源。
总之,中国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应不晚于1835年即在西方得以译介传播,其后历经近200年的持续推进,其间不断地涌现出各类翻译与研究成果,而“异”成为欧美汉学一以贯之的核心论题与贯穿性主线。从早期对“异”的曲解,至观风俗之不同,再至对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等深层次问题的探寻,《聊斋》之“异”在跨文化语境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涵与价值。围绕“异”所出现的各种跨文化表征,一方面是欧美汉学家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对《聊斋志异》所作出的叩询与追问;另一方面,这些文化表征也进一步揭示了《聊斋志异》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内涵,推动了该书在海外的传播,使得《聊斋志异》进入了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
作者简介

任增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与汉籍传播影响,著作有《英美聊斋学研究》(专著)、《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合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译著)等。